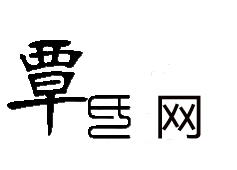关于唐崖土司属覃氏渊源的考证
-
三、关于“唐崖土司属覃氏是蒙古族后裔”的
错误论据种种
“刘吴论”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,也提出了一些论据,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论据的真伪,以进一步证明“刘吴论”的虚假性。
1、“木雕神像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引述,解放前唐崖覃氏有的在其神龛上除供奉“天地君亲师”位外,还特地供奉木雕的“铁木乃耳”神像,并且认为这是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最可靠的证据。
大家知道,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,是一个民族深层意识的层面,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强的传承性。作为一个民族,蒙古族的图腾崇拜,主要是“狼图腾”、“鹿图腾”和“鹰图腾”,祖先崇拜主要是供奉“成吉思汗”(铁木真),信奉的宗教是萨滿教并主张对宗教兼收并蓄,日常祭祀主要是“祭敖包”(以土堆代表天地),没有以其他个别的人像作为民族的象征的。这就说明,以其他个别的人像作为民族的象征,不是蒙古族的民族传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应该尊重蒙古族的民族传统。
至于唐崖覃氏中有人家中曾供奉木雕的“铁木用耳”像,这只能作两种解释:一是,“铁木乃耳”一词,本身是唐崖覃氏某个祖先的蒙古语翻译(后文还要说到),家中供奉他以示不忘记这个覃氏祖先;二是,唐崖覃氏中个别小支系,曾与元代驻守唐崖的蒙古族中个别人有某种恩惠关系,覃氏族人本来是很讲究感恩的,供奉这个人的木雕像以示不忘记他的恩德。这两种解释都是说得通的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这就表明,以解放前个别唐崖覃氏族人家中曾供奉“铁木乃耳”木雕像,作为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“最可靠的证据”,由于它不符合蒙古族的民族传统,这个证据就不能成为有效证据了,何况还有上述说明的其它可能呢。
2、“语言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在论述中提到,唐崖覃氏在语言方面,客观上存在着由蒙古语向土家语转化,再由土家语向汉语转化的历史链条。
勿容讳言,在唐崖《覃氏族谱》中,确实存在着蒙古语——土家语——汉语的痕迹,难道这就能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人后裔吗?
前面谈到,元代统治者(蒙古人)入主中原后,实行的是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,蒙古语是其官方语言,他们强迫“南人”运用蒙古语言,这是在所难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这样,在覃氏族人和覃氏族谱中留下某些蒙古语的痕迹,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
在蒙古人的高压统治下,处于社会最低层的“南人”被迫使用蒙古语,在历史上留下了某些蒙古语的痕迹,论者就以此为据,说这人是蒙古族的后裔,这道理成立吗?这个道理如果一旦成立,岂不是要闹出很多的令人不可言状的笑话吗?
3、“碑文材料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在论述中又提到:“唐崖土司皇城遗址的墓葬群中,早期的墓葬基本上没有碑文,后期的皆有碑文,它说明这支蒙古族与当地土著覃氏融合时,汉文化水平还很低”,并以此证明这支覃氏是蒙古族后裔。
关于碑文问题,大家去考察一下吧:各土司的土司主在前期大抵都没有碑文的,这一方面是某一个几个时代的习俗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密。这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很低,并且还进一步证明他们是蒙古族后裔呢?
忠路土司第十二任司主覃进孝(明末清初人),是明朝皇帝封授的“太子太保、忠义侯、威武上将军”,他在去世时,民间传说是48驾灵轿上路,埋葬了48个地方,但都没有碑文。忠路土司属《覃氏族谱》上记载的葬地墓,也没有碑文,解放后当地人都看到的。请问“刘吴论”者,能够以此为据,就说忠路土司属覃氏的汉文化水平“很低”,并以此证明忠路覃氏是蒙古族后裔吗?
如果说唐崖覃氏真是蒙古族后裔,即使他们的汉文化水平“很低”,难道就不能用蒙古语作碑文吗?更何况如“刘吴论”者说,他们在一定时期还是“统治者”、“征服者”呢。
企图用“碑文材料”之类来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,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。
4、“能征善战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在论述中还提到:“唐崖土司是我国西南地区以武功著称的土司之一,尤其在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区颇具影响”,“从唐崖土司能征善战来看,其一世祖为将门之后真实可信”,并以此作为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证据之一。
不可否认,以成吉思汗、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,当年确实是能征善战的。
但是,君不见土司时期,鄂西各土司都是“以武功著称”、“能征善战”而打出自己的一片领地,获得历代封建王朝认可的呀!当明王朝的军队在倭寇面前无所作为的时候,而以容美土司主为头领、鄂西各土司土兵参与的鄂西土兵把倭寇打得落花流水,立下了“东南第一功”,受到了明王朝的特别嘉奖。这能证明他们都是蒙古族的后裔吗?
要说到武功,唐崖土司虽有一定建树,多次获得明王朝的嘉奖,并赐“大坊平西将军”和牌楼上“荆南雄镇,楚蜀屏翰”八字。但是,这些封赏可以与忠路土司主覃进孝获封的“太子太保、忠义侯、威武上将军”相提并论吗?因此,就论武功,唐崖土司也不一定是最强的呀。
说到底,以“能征善战”的武功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的后裔,首先是论据失实,其次这个论据也是不充分的。因此,此据无法证明“刘吴论”的观点。
5、与其他土著覃氏的“对比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在论述中还用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关于“世系”和“字派”的对比,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。如此的“对比说”,就更不值得一谈了。
就“世系”而说,鄂西其他土著覃氏先代同出一源,当然相同。而唐崖覃氏的先代名字用的是蒙古语,当然就不好比了,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若以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而论,在元史及相关的典籍中,都没有铁木乃耳(任平肩之职)、颜伯占儿、脱音贴儿(任宣慰使之职)和福寿不花的名字。仅有一个文殊海牙的名字,但他却在元末陈友定割据闽中八郡时任陈的“参政”,这与唐崖土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从这点出发,也可以论断唐崖覃氏不是蒙古族的后裔。
笔者赞同覃章梁先生的考证,唐崖覃氏与鄂西土著覃氏主流一样同为覃伯坚的后裔,与覃启处送相关的前几代应为:覃汝先-覃伯坚-覃普诸-覃散毛-覃启处送,这样就通顺了,也与唐崖覃氏历代相传的先代为官的故事大体相当。
至于“字派”,鄂西土著覃氏的各土司属宗支,在创修和续修族谱时,都是立足于自己的宗支,没有联络相关宗支,致使各土司属宗支的字派各不相同,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只有施南土司属宗支在乾隆45年创修族谱时,因为湖南石门覃氏有人在修谱处教书,施南土司属宗支的字派就借用了石门覃氏的字派。用“字派”不同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,这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。
6、“体质特征说”。有持“刘吴论”观点的人认为:“唐崖覃氏曾保留着蒙古族体质的一般性特征”。
人们都看到的,居住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体质、体型,与蒙古族没有明显的区别。因此,用唐崖覃氏中某些人的部分体质、体型特征,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,这是没有道理的。